党史学习教育丨核工业功勋:研究大宇宙与小原子的“先生”们
发布时间:2021-06-03 信息来源:默认部门


1993年,杜祥琬(左一)与朱光亚(左三)等在罗布泊试验场
有一次杜祥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,里面的小朋友天真地问:
“杜爷爷,我们将来长大了是不是把氢弹做得威力更大?”
杜祥琬回答:“现在的氢弹已经是几百万吨了,你们将来不需要把它做得更大,你们及与你们同龄的全世界各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代人,如果有共同的目标,就一起努力禁止、销毁核武器,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。”
接受采访时,杜祥琬语重心长地说:“现在的青年朋友要理解,当年的‘邓稼先’们搞核弹是被迫的,是当时国际局势需要他们去做。他们都是很有理想的科学家,在他们的心目中,掌握核武器技术,不是为了打仗,而是为了和平。
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发表国家公报时就明确说‘中国主张全面禁止、彻底销毁核武器’,在那之前,国际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说过。奥巴马因为提出‘无核武世界’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,其实这个理念中国1964年就提出来了。”
“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”
“我快60岁的时候,90岁的王淦昌告诉我:‘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!’当时我只当是他对我的一句平常的鼓励。后来我才意识到,王老本人从60岁到90岁,30年里,他的确从头开始又干了6件大事,而且都是国家级的大事。1969年负责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测试时,他62岁。”
今年6月,8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核工业功勋人物杜祥琬老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笔者采访时说。
20多年来,在王淦昌老先生那句话的“点化”下,杜祥琬仿佛真的进入了第二个青壮之年。
1997年,60岁的他当选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。2001年,任863计划先进防御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。2002年,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。负责主持院士队伍建设、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咨询研究等工作。2006当选俄联邦工程院外籍院士。晚年的杜祥琬继续为国家“核”与“光”贡献余热,承担了数个学术兼职,至今仍在做能源领域的战略研究。
“大大的宇宙没学成,学了小小的原子核”
杜祥琬高中时喜欢去阅览室看一本名为《知识就是力量》的杂志,里面有很多天体、天文学的故事,非常吸引人,他从中感受到宇宙的魅力无穷,立志要学天文学,高考填报志愿也是南京大学的天文学系。结果却被国家选入留苏预备生,因为当中有两年暂时还不能去苏联,就让他们先选读国内的大学和专业,他选了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。他解释说:
“我觉得那是离天文学最近的学科。”
国家选拔出来30个年轻人去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(为苏联搞核武器培养人才的地方),其中就有杜祥琬,他们的专业也是国家定好的——理论核物理。

1960年2月,在莫斯科郊外冬令营
“后来小朋友们听我的故事时感叹说‘大大的宇宙没学成,学了小小的原子核’。我说你们看看,原子的结构,是里面一个核、外面围绕着一些电子,是不是跟太阳系很像?原子核很小,太阳系很大,但物理学很多地方都是相关联的,进入了原子核的领域后,我觉得也很有趣味,人呢,干事情一定要感兴趣才能做好!”
在苏联学习的时候,杜祥琬并不知道国家要他干什么。毕业前夕,他跟一个苏联同学在餐厅边吃边聊。
“杜,你在这儿学核物理,回去有啥事可干呢?”
这位同学的口气里,透露出他心目中的中国还停留在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的没落清朝。
刚好当天晚上,莫斯科广播电台播了一条一句话的消息:“今天下午,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。”
第二天上午杜祥琬去答辩毕业论文,在走廊又碰到那位同学,他热情地跟杜祥琬打招呼:
“杜,祝贺你!”
回忆那一幕,杜祥琬仍激动不已,国家的强大带来个人的尊严。学成回国的杜祥琬,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“童顽”邓稼先
谈到老领导邓稼先,杜祥琬提到了一句诗“有的人死了,可他还活着”!
“酷爱生活似童顽,浩瀚胸怀比草原。”
平常也爱写点小诗的杜祥琬在一首名为《悼老邓》的诗里写到。
“真正的核工业功勋人物,邓稼先是当之无愧的。”杜祥琬郑重地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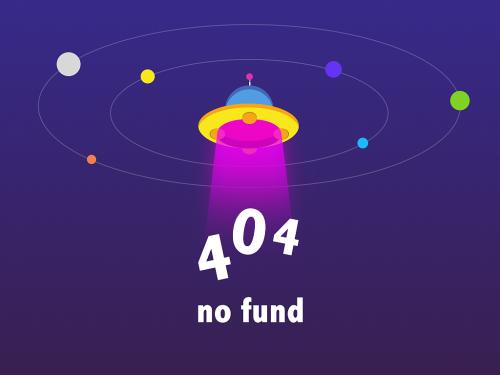
1993年,杜祥琬在核试验场
当年,在位于梓潼县长卿山下的九院老院部(现在的两弹城),杜祥琬和邓稼先也算是北京“老乡”。只要礼拜天有点空,杜祥琬就会去看邓稼先,邓稼先总是边打开自己的柜门边问:
“巧克力?”
“有时,老邓会带我一块翻过长卿山去梓潼县城逛逛,路过潼江的漫水桥时,他总要拉我到桥附近的一家小饭馆:‘咱俩吃鱼’。在北京,我们经常晚上去国防科工委汇报工作,汇报完已经半夜了,大家肚子都饿了,就会说:‘老邓请客’。”
杜祥琬又讲到了邓稼先的一件小事:“有一次,我为了弄清楚带电粒子在介质里面传播的能量衰减的公式,去借阅了一本《物理评论》杂志,发现有人在相关内容旁边写了字,我一下就认出那是老邓的笔迹。那些论文往往说不难导出如下公式,但却不明确推导出。邓稼先在研究思考的时候忍不住把推导公式写在旁边。我能想象,他当时钻研问题时那种忘我投入的状态。”
老于给老邓打电话:我们抓到牛鼻子了!
从莫斯科毕业回国后,杜祥琬进了当时的核物理研究院理论部,部主任就是邓稼先。
“当时,理论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,相互之间不称头衔,只以老小相称。我觉得这不仅是个称呼上的问题,它是一种温度、一种氛围!显示了这个单位人和人之间和谐、平等的关系,是很有意义的一种团队建设形式。”杜祥琬说,“我第一次与邓稼先的近距离接触就是氢弹原理试验。”
氢弹的物理反应有几个阶段,比原子弹更复杂。我们小组的任务是核试验诊断理论计算,就是通过核试验的测量数据,判断里面发生的是不是氢弹爆炸。这就涉及一系列物理量的测试项目。
全当量氢弹爆炸威力大,需要高空爆炸,为了保险起见,理论部决定先做一次低当量的氢弹原理试验,为爆炸试验人员提供可参考的测量与判断依据——什么量程范围算成功。
突破氢弹原理时,整个理论部的人,没有谁具体知道氢弹的结构和原理,以邓稼先等为代表的当时的领导就采取学术民主的方式。年龄大的四五十岁,年轻的二十来岁,大家坐一屋子,不论年龄、职务、资历,谁有什么想法就直接上台说,因而当时叫“鸣放会”,允许大鸣大放。这样一来,大家积极性都很高,你来我往,几十种想法就出来了。大家提出的想法经过分析,最后归纳了四个有可能成功的方案,由于敏带领一些人去计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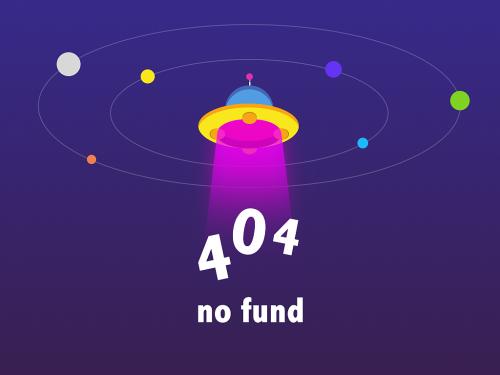
杜祥琬与于敏(左)
“我们常看到于敏一副眉头紧锁的样子,是因为他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思考问题,为此还睡不着觉,要靠吃安眠药,有时要吃两片。
老于和老邓一边研究思考,一边写成讲义给大家讲课。经过计算,最后判断其中一种可行,老于就给老邓打电话‘我们抓到牛鼻子了!’当时大家的压力都很大,老邓一听就意会了、高兴了,氢弹的研究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当晚老邓开心地喝醉了酒,他长期承受着巨大压力
1966年12月,杜祥琬等三人按照邓稼先的安排从上海去新疆交数据。当时,从上海到新疆没有客机可坐,需要坐绿皮火车。正值文革时期,火车走到宿迁时被强行停下来耽搁了两天,他们再坐火车去都来不及了。碰巧,当时的副院长朱光亚要坐专机到试验基地去,就让他们搭乘自己的专机,他们才及时赶去了基地。
在基地,他们住和工作都在一个帐篷里,里面是铺着木板、上面放上帆布的大通铺,晚上他们在大通铺上睡觉,白天就在上面工作,利用实验前的时间再一次复算理论计算的结果。
没有计算机,他们只能用计算尺、手摇机,一秒钟大概算几次。
临近试验的最后几天,他们搬进试验场附近由解放军搭建的帐篷,一个帐篷三个上下铺,住六个人,夜里很冷,需要生起一个小煤炉子。
“在那里,不管领导还是我们计算数据的,大家一心一意就是想让试验成功。”杜祥琬说。
氢弹爆炸仅凭外观无法判断是否成功。凭靠氢弹爆炸涉及的两个速报项目的测量数据,试验一结束,他们就确切得出了成功的结论。氢弹原理试验成功,意味着半年后全当量的氢弹爆炸试验就很有把握了,于敏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,说那就是氢弹爆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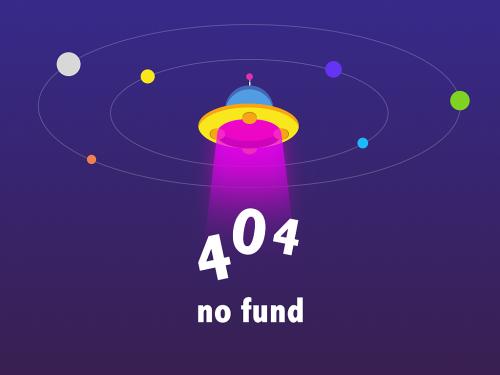
杜祥琬与朱光亚(左)
“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实际开端应该是1966年12月28号——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时间,但这又不能公开说,朱光亚琢磨了半天,在报告里写了一句话‘中国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’,周总理同意了。”杜祥琬说,“当晚老邓开心地喝醉了酒,他长期承受着巨大压力。”
第二天开了简单的庆功会之后,他们就在现场开始讨论下一步的全当量核试验应该怎么做。回到北京后,整个理论部的人都跑到食堂会议室去开会,大家都希望赶在法国人前面做成氢弹试验。
贴到院门口地上的号外
核武器的中国道路有两个特点:一个是用时最短,一个是花钱最少。但关于研制费用,许多老百姓也有误解。
“有一次,我去一个宾馆参加核数据大会,吃饭的时候,旁边一位参加其他会议的女士一听我们是跟核有关的,立即抱怨说‘都是你们搞核试验,把国家的钱都花了。’
得知对方是上海人之后,我告诉她:
你知不知道宝钢花了多少钱?我们研制核武器花的钱还没有宝钢多,只用了美国2%的研制费用。”
“氢弹全当量试验我们没有在现场,有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私下得知了我们这个院子就是干这个工作的,氢弹爆炸当天,有人把人民日报套红的号外贴到我们院门口的地上。”谈起这个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情景,杜祥琬依然兴奋地笑出了声。为了符合保密要求,两弹功臣们致力奉献,平常什么也不能说,但感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,功臣们的内心也是欣慰的。
一生做一件事,像挖井一样
杜祥琬一生的研究涉及天文、数学、核物理、激光、能源研究等多个领域。被问及感受时,他说:“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就做一件事,他就会像挖井一样,可以做得更深一点。我每次并不想转领域,但国家需要的事,我觉得有意义,就去做了。我所参与的863计划看似离开了核去搞激光,实际上仍然没有离开核的背景,或者某种程度上还是为了核。”
“有很多的院士是在国外进修学习过的,国外给他们很好的工作条件,但他们坚持要回国。
美国人曾开玩笑说我们都有一个‘m’,他们爱的是 money(钱),但我们爱的是 mother(母亲)和motherland(祖国)。
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懂得钱的重要,我们的国家也要富裕起来,这正需要我们去为祖国而努力。”

1959年,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动手训练课程:电焊
作为一名科技领域的老前辈,杜祥琬院士在采访的最后寄语青年人:要树立崇高的理想来引导自己的一生,理想可以出动力、出精神、出素质,使你的胸怀宽阔,开创美好的未来。(中国核工业)